
王安忆,生于1954年,当代作家、文学家。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代表作《长恨歌》《流逝》《小鲍庄》《纪实与虚构》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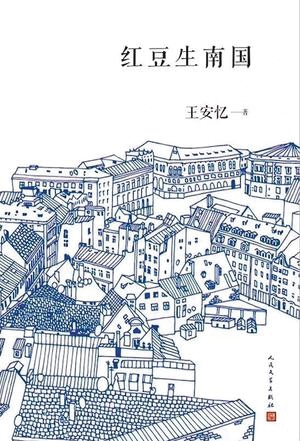
《红豆生南国》
作者:王安忆
版本:人民文学出版社
2017年6月

《仙缘与尘缘》
作者:王安忆
版本:人民文学出版社
2017年6月
近日王安忆中篇小说集《红豆生南国》悄然面世,纯白色封底,蓝线素描的欧洲小镇,很贴切地展示了这本书的特质:它不是浓烈跌宕的情节型小说,而是细腻的工笔小说。对致力于长篇创作的小说家来说,中短篇小说更像是在奔赴下一个长篇之前的休息和热身。去年出版的长篇《匿名》对于时空、文明的宏大思考和繁复思辨,无论是对王安忆,还是对喜欢她的读者而言,无疑都是一次陌生的冒险之旅,赞赏她勇于突破的有之,失望于她繁琐空泛的有之。而《红豆生南国》,又一次回归到针脚绵密的日常书写之中,回归到我们熟悉的那个“王氏风格”。
1 写都市人生
希望还原他们说话的方式
此书包含三个中篇:《乡关处处》《红豆生南国》《向西,向西,向南》,对应三个城市:上海、香港、纽约,写了三组群像:上海钟点工、香港男人、纽约华人。这三个城市无疑都是世界级大都会,高楼大厦之下,人潮汹涌,多少人生故事滋生其中。写都市日常人生,正是王安忆的拿手好戏。
有个细节颇有意思,三篇小说都标有写作的时间和地点,分别是:2016年元月25日纽约;2016年4月9日纽约;2016年10月27日上海。2016年她客居纽约时写上海和香港,回到上海后回头写纽约。在一个城市写另外一个城市,时空的距离就有了,能够以远观的审视态度来写。而在纽约的生活,让她对美国海外华人的生活有了细致的了解。《乡关处处》《红豆生南国》和《向西,向西,向南》颇不相同。在语言的运用上,前两篇语言往回缩,四字结构,颇有古白话的凝练之风,而到了第三篇恢复到日常普通话的节奏。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这一点:“可能还是和题材有关系。尤其是第二篇,《红豆生南国》,因为我写的是香港社会,香港人说话其实很有古风的,但我本人不会说广东话,当我很客观写他们的时候,还是会注意希望能还原他们说话的方式。到了第三篇就是普通话的叙述。第一篇是写绍兴保姆,绍兴人说话也和普通话体系不大一样。普通话的叙述和地方上的叙述不一样,但我也不企图像金宇澄那样(全用地方话来写)。”
王安忆之前也写过上海外来务工人员,比如说《民工刘建华》写木工,这次她写了钟点工月娥。王安忆笔下的女性,向来都是生命力顽强坚韧,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困顿,都能一步步打拼出一番新天地。月娥也是。她有着朴素的生活观,每一点攒下来的收入,都能让她觉得生活有盼头。同时她也接触到了繁华的上海,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上海人,甚至与其中一些人有了感情的维系。“幸亏,幸亏走出来,看到大世界。倘若不是这一步,少赚钱不说,还错过多少风景,岂不可惜死!”夜晚忙完,她骑着电动车穿行在上海的街道上,内心涌动着的是自豪感。
2 关注日常生活
从杂乱琐细中品出诗意
王安忆小说中有个常见的人物模式:女强男弱,在这本书也有体现。《乡关处处》中月娥与丈夫,女方在上海打拼,男方固守家中,家里主要经济收入还得仰仗女方。而在《红豆生南国》中,男人则在情感关系中处于弱势。这个香港男人骨子里是文艺青年,早年随时代风云鼓动,写了很多热情洋溢的文章,后来运动落潮之后回到生活之中,结婚生子,日子却并不如意。这篇小说中提到的两个女人都是香港男人的至亲之人,一方是他的养母阿姆,一方是他的妻子(之后是前妻)。婆媳不和,他夹在中间,备受折磨,“千真万确,女性是他天然的债主,他生来就是为了还报她们的施舍”。
“女性是他天然的债主”,是王安忆诸多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母题,这个“他”可以是《一家之主》里的新加坡男人,可以是《长恨歌》里的萨沙,也可以是“三恋”中的男人们。女性在这种关系中处于强势,她们主动地争取自己的命运钥匙,相比之下,男人都孱弱苍白,习惯往内里缩。《红豆生南国》这样写道:“他惧怕婚姻,婚姻这一种恩惠,比生恩养恩又有所不同,它包含情欲的施舍,不啻是人生的奢物,更有传宗的给予。想他这样,出生多余的人——被送养的命运多少有这么一点意思,有延续子嗣的价值吗?他简直在强取豪夺,剥削造物,前债还未还清,哪敢再续后账?”
再说到这两篇小说的题目,也体现出王安忆一贯的偏好,她往往喜欢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求灵感,如《长恨歌》《上种红菱下种藕》《桃之夭夭》《天香》等。这次也不例外,《乡关处处》出自崔颢的《黄鹤楼》:“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《红豆生南国》出自王维的《相思》:“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。”古典诗词,人生况味,高度浓缩,王安忆笔下的人物,却是从杂乱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品出诗意。
说到日常生活,王安忆非常爱提到一个词——“芯子”。在《长恨歌》中,她写王琦瑶的生活,找到她的性格逻辑,顺应时代的变动而走,然而生活的日常是最里层的,人在这个层面上是踏实地活着,所谓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。她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,形成了自己的美学。小弄堂里狭小格局里有大文章,如何布局,人们如何相处、生活,人情世故如何微妙细腻地展开和变化。她写起这些来,可谓是“耽溺”。《乡关处处》和《红豆生南国》是这种“耽溺”的延续。
3 人生如寄
从世俗中超拔出来,酝酿生存的诗意
《向西,向西,向南》写上海女人陈玉洁和丈夫跟随改革开放大潮在生意场上一路打拼,挣到足够多的钱,来到纽约,买下房子。紧接着是生活的崩塌,丈夫出轨,女儿疏离,打拼半生,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。这篇小说从柏林到纽约再到加州圣迭戈,空间跨度大,涉及的材料也多,前半段稍显滞涩,后面写到两个女人的相处,一下子又流畅熟悉起来。
对于女性情谊之间的刻画,也是王安忆的拿手好戏,比如《长恨歌》中的王琦瑶与她的女伴,《弟兄们》中的三个好姐妹,《天香》中的小绸妯娌。女性间的感情往往是无关情欲的亲密无间,其细腻微妙往往也是王安忆着力甚多之处。这篇小说对两个女人之间的交流,有细致的描写,读来颇为动人。
读完三篇小说,有一种“人生如寄”之感。钟点工在上海,千辛万苦,终究难以扎根下来;香港男人、至爱之人,都让他疲惫不堪躲闪不及,虽然在从小生长的城市,不也如风吹浮萍一般吗?而纽约的这两个女人,跨越半个地球,相遇之时都有心伤……
原有的生活都已经远去和崩塌,未来的生活还不可知,只能看个人造化。王安忆喜欢把这些寄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。这三篇小说中,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进城务工、香港回归、国企改制、金融风暴……人寄存于时代之流中,时代变幻,人生随之变幻。在《向西,向西,向南》结尾,原来在柏林开书店的潘博士光顾了陈玉洁和徐美棠的中餐馆,潘博士“发现自己,最适合的生活是,做一名游僧。开车行驶在西部的沙漠,仙人掌一望无际,太阳照耀大地,前方是地平线,永不沉没”。这或许也是王安忆笔下很多人物的自我放逐之旅。
王安忆说过:“我觉得小说就是要讲一个故事,要讲一个好听的故事,不要去为难读者。”还说过:“我写了这么多的小说,当然是可以将世俗的东西安排得非常好的,但如果仅仅让我写一部世俗小说我是没有兴趣的。”《红豆生南国》可谓实践了她的想法,三篇小说都是“好听的故事”,虽然都涉笔世俗生活,可又能从世俗中超拔出来,酝酿出生存的诗意来。
□邓安庆


新闻热点
新闻爆料